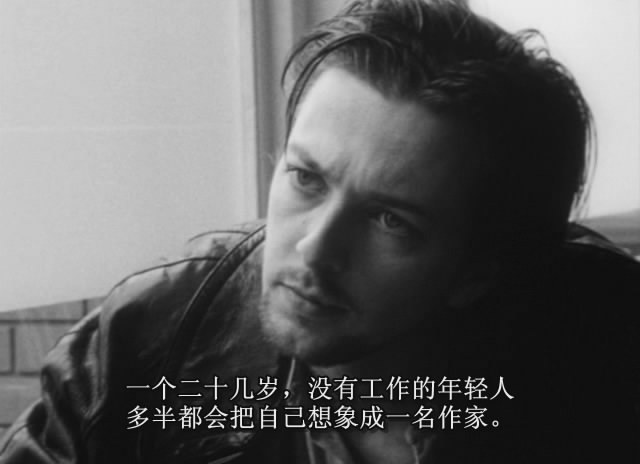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俊 北京报道
近年来,大厂的竞业限制协议频频登录热搜。这一项被用于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制度设计,出现了边界适用的问题。
今天(4 月 16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第四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便有关竞业限制,月入 3500 的保安小哥,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内附竞业限制条款,离职后到另一家保安公司入职,结果被认定违反竞业协议。最终仲裁认为,主体不适格,竞业限制条款无效。
最高法、人力资源部指出,当前一些行业、企业出现了用人单位滥用竞业限制条款限制劳动者就业权利的情况,侵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影响了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损害了正常的营商环境。并要求,各级裁审机构需对竞业限制条款进行实质性审查,既要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因不适当扩大竞业限制范围而妨碍劳动者的择业自由。
主体不适格,竞业限制条款是否有效?
某保安公司主营业务是给商业楼宇、居民小区提供安全保卫等服务。2019 年 3 月,某保安公司招聘李某担任保安,双方订立期限为 2 年的劳动合同,工资为 3500 元 / 月。劳动合同约定保安的主要职责为每日到某商业楼宇街区开展日常巡逻安保工作,同时内附竞业限制条款,约定 " 职工与某保安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 1 年内不得到与该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就职,职工离职后某保安公司按月支付当地最低月工资标准的 30% 作为竞业限制经济补偿。职工若不履行上述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违约金为 20 万元 "。2021 年 3 月,双方劳动合同到期终止,李某未续订劳动合同并入职另一家保安公司担任保安。某保安公司认为李某去其他保安公司担任保安违反竞业限制约定;李某认为自己作为保安,不了解也不掌握公司的商业秘密,自己不是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适格主体。某保安公司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最终仲裁委员会驳回某保安公司的仲裁请求。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是否为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适格主体。
根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有权利与 " 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 " 约定离职后竞业限制条款,竞业限制的人员范围仅限于 " 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因此,用人单位与 " 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 " 以外的其他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应当以该劳动者负有保密义务为前提,即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职务或岗位足以使他们知悉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
本案中,李某的主要职责为每日到商业楼宇街区开展日常巡逻安保工作,其所在的保安岗位明显难以知悉某保安公司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某保安公司亦无证据证明李某具有接触公司商业秘密等保密事项的可能,因此李某不是竞业限制义务的适格主体。某保安公司与李某约定竞业限制条款,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竞业限制义务适格主体的规定。因此,竞业限制条款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对某保安公司要求李某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的请求,仲裁委员会不予支持。
最高法在评述时指出,竞业限制是在劳动立法中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一项制度安排,本意是通过适度限制劳动者自由择业权以预防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进而维护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环境。但当前一些行业、企业出现了用人单位滥用竞业限制条款限制劳动者就业权利的情况,侵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影响了人力资源合理流动,损害了正常的营商环境。
各级裁审机构在处理竞业限制争议时应当坚持统筹处理好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关系的原则,对竞业限制条款进行实质性审查,既要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因不适当扩大竞业限制范围而妨碍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既要注重平衡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又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实现竞业限制制度的设立初衷。
用人单位能否因女职工怀孕调岗降薪?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还有一起用人单位变相调整工作岗位降低孕期女职工工资及福利待遇的案例。
赵某于 2022 年 1 月入职某科技公司任工程师,双方订立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期间分为参与具体项目期间与等待项目期间,其中参与具体项目期间赵某的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 3000 元(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加项目岗位津贴 14000 元;等待项目期间赵某仅领取基本工资。2023 年 2 月,赵某告知某科技公司其怀孕事实,某科技公司未与赵某沟通协商便直接向赵某所在的项目组宣布 " 赵某退出所在项目组 ",赵某反对无果后未再上班。此后,某科技公司主张赵某未参与项目并按照 3000 元 / 月的标准支付赵某孕期工资。赵某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某科技公司按照 17000 元 / 月的标准补齐孕期工资差额。
最终仲裁委员会裁决:某科技公司按照 17000 元 / 月的标准补齐赵某孕期工资差额。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用人单位能否因为女职工怀孕调岗降薪。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19 号)第五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怀孕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 ",明确 " 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 " 的前提是 " 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 "。因此,如果孕期女职工能够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尊重并保护女职工的劳动权利。
本案中,某科技公司要求赵某退出所在项目的行为,既不符合双方劳动合同约定的等待项目期间的情形,也未征求赵某本人的同意,更未经医疗机构证明赵某存在 " 不能适应原劳动 " 的情形,属于违反《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规定,变相调整孕期女职工岗位的情形。该公司以赵某未参与项目为由降低赵某孕期工资标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因此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某科技公司按照赵某原工资待遇 17000 元 / 月的标准补齐赵某的孕期工资差额。
最高法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要求,我国多部法律法规对保护女职工劳动权利与身心健康作出了特别规定。实践中,用人单位在开展日常用工管理时应注意依法保护女职工尤其是孕期、产期、哺乳期(以下简称 " 三期 ")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不能通过变相调整工作岗位、提升工作强度等方式侵害 " 三期 " 女职工的劳动权利,也不能违法降低 " 三期 " 女职工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同时,女职工也应科学评估自身身体状况,正确看待不能适应原劳动等特殊情形,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合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