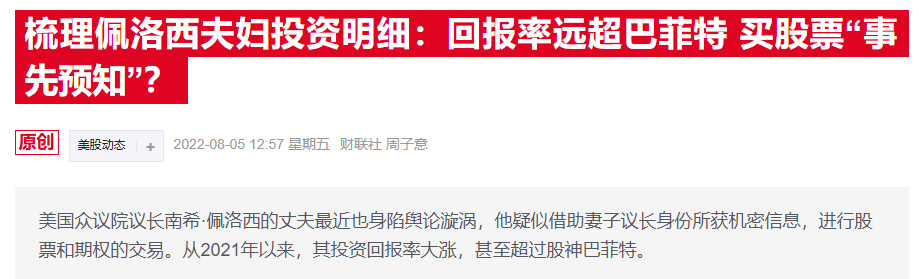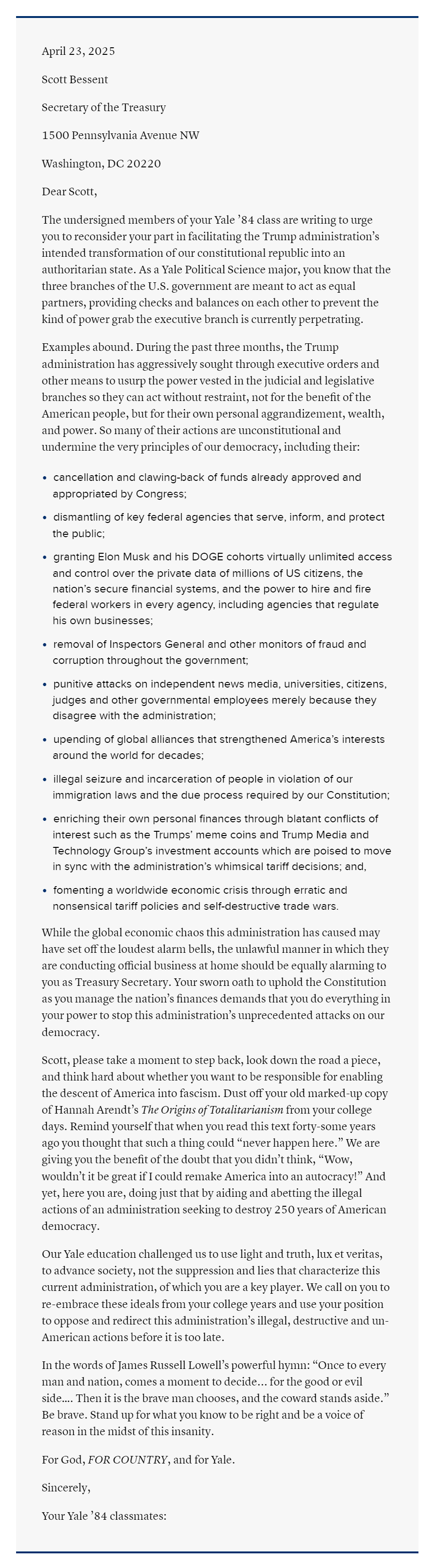2025年3月,以古代日本为背景的《刺客信条》系列终于推出正统续作《刺客信条:影》(以下简称《影》),粉丝等待这一天的时间很可能比等待《GTA 6》还久。早在十多年前的《刺客信条3》中,日本刺客兄弟会的彩蛋刚刚埋下,就有无数玩家翘首以盼着“扮演忍者”的游戏体验。然而育碧却迟迟没有兑现这个诱人的承诺,一再雪藏“日本刺客”题材而错失了最佳推出时机,以至于这个曾经惊才绝艳的系列在漫长等待中被其他游戏反复模仿、变得司空见惯。当《影》终于在今年发售,玩家早已不再惊喜,反而出现了一片意料之外的争议。
但客观地说,《影》仍然是一款值得认真对待的作品:它不完美但也足够用心,将东方美学、角色塑造与叙事张力结合到了一起。就像任何一个成长在强势家族阴影下的孩子一样,《影》也无法逃脱来自家庭的原罪——模板化的任务结构、延续至今的系统惯性,以及注定引发争议的文化表达方式。本文将先基于笔者个人的主观游戏体验,讨论它那些“好”和“不够好”的地方,再针对有关《影》的风波和节奏,探讨这些节奏背后的文化与身份焦虑。

为《影》正名:体验派对风评的反驳
《刺客信条:影》在发售前遭遇了一场舆论狂风,它甚至还未正式发售,就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被定罪。一部分网友们对弥助的肤色大做文章,对“双主角”设定发难,对育碧的“文化挪用”和“不尊重日本历史”标签疯狂刷屏,最终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还未通关,即下定论;未曾试玩,却已否决。
本文并不打算为育碧粉饰太平,作为一名长期关注这一系列的玩家,笔者十分清楚育碧的系统惰性、叙事套路和工业罐头般的内容堆积。但正因如此,《影》在实际游戏体验中带给玩家的某些真实、鲜活和用心的部分,反而变得异常珍贵。在笔者的游玩体验中,前十几个小时的游戏节奏紧凑得令人惊讶——不是标准化的无聊“教学序章”,而是用真正意义上的剧情推进快速引出主要角色。故事从弥助获得织田信长赏识、成为战国乱世中的“外来武士”开始,他率军进攻伊贺,引出了另一位主角奈绪江——一位生于忍者世家的少女。随着主叙事视角的转换,我们见证了奈绪江家园被毁、父亲惨死,她在僧人与男孩顺次郎的帮助下逃出生天,从此踏上复仇之路。
在这一部分游戏体验中,游戏呈现给玩家的观感颇为不俗——每一步都节奏明快、情绪扎实。剧情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本能寺之变,在这场火与血交织的夜晚,奈绪江与弥助的命运第一次正面交锋,也奠定了整个游戏的情感基调:复仇与悔恨。优秀的场面调度和恰到好处的配乐,既完成了对这个经典历史事件的重写,也靠调动玩家情绪带过了一些为了合理化剧情不得不妥协的情节bug。
紧接其后的“交野城雨夜”一幕中,奈绪江、弥助和顺次郎的三人同台进一步升华了这部游戏的情绪基调。以往的《刺客信条》系列暗线专注于“两个影子政府之间的争斗”,《影》则关注“原谅一个知错之人,是否也是一种正义”,角色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在这段情节中获得重新阐释,不再被简单归类为“敌我”或“黑白”。

如果说在一部成熟的游戏中,玩法是它的骨架、剧情是血肉,那么动作设计和美术风格就是它的皮肤与气息。在这一点上,育碧在《影》中所展现的技术力与资源投入值得特别关注。以主角奈绪江的刺杀动作为例,育碧难能可贵地弃用了系列祖传的刺杀动作模组,针对“忍者”这一题材,彻底重新设计了一套迅捷流畅的动作系统,成功地塑造了符合日本流行文化想象的“忍者”形象。
《影》在视听审美方面是下足了功夫的,在克制中打造出一种别样的美感:干净、锐利、富有力量感的现实主义东方美学。绝大多数场景保持了清晰明快的写实质感,光影处理真实、打光恰当,但在特定时刻(九字真言、必杀技)突然切入黑白、水墨的风格化镜头——这种对东方美学的仪式性使用,制造出一种美术节奏感,让视觉融入剧情与玩法中。
在众多系统机制中,笔者最喜欢的是奈绪江的“九字真言”。这个系统乍看只是个QTE小游戏:角色打坐、屏幕出现四个按键提示、玩家重复操作……但随着逐个正确输入,画面开始从写实慢慢向水墨风格过渡,音效从环境噪音退到冥想钟声,按键提示也逐渐消失,仿佛奈绪江正在进入一个脱离外界逻辑的精神空间,而你也随之进入。这是一次绝妙的具身化体验设计,不是“我看着她冥想”,而是“我必须通过冥想动作,与她同步呼吸”。通过对角色认知的体验接管,玩家逐步与奈绪江合为一体。
这可以说是《影》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之一:当育碧决定认真做一个系统,它仍然可以把玩家、角色与美术语法三者编织成一个情绪整体。只可惜这样的用心在本作中并不普遍。你越是感受到这些设计的优雅与精妙,就越容易意识到它们的稀缺性。我们可以在“九字真言”中与角色共感,但我们也将在更多的游戏流程中,面对育碧那条熟悉的路径——重复、堆料、过度模板化。

“躺在祖业的功劳簿上”——《影》的系统保守性
奈绪江与弥助、顺次郎遵照伊贺传统宣誓重建“刺客一揆”——这是游戏中的一场仪式性高潮,也是育碧精心设计的情感引线。这场仪式似乎也是《影》与玩家的“婚礼”——浪漫的恋爱结束了,欢迎回到寻常人家的柴米油盐。
在前十小时的游戏过程中,《影》确实为玩家提供了一段蜜月期:节奏紧凑、剧情推进清晰、角色成长线动人。玩家可能会以为“这次真的不一样了”,它不再是那个“年货信条”了。但随着“刺客一揆”的“复建仪式”结束,浪漫也随之退场。玩家会突然发现,等在你面前的是一张铺满任务标记的地图、数十个可疑的任务目标、每个暗杀目标又被切割成两个前置任务,每一个前置任务的NPC必然会对主角抱有怀疑,而他们的信任都必须用一次讨伐敌人、清营地、找遗物来换。
熟悉的感觉都回来了——那个满屏圆圈式的暗杀名单和“大地图分区制霸”的任务结构,玩家已经不能再熟悉了。从《奥德赛》里的“古希腊秩序神教大扫除”,到《英灵殿》里的“维京版名人狙杀行动”,我们终于在《影》里等来了日本战国版“区域大名清除计划”。育碧似乎决心证明自己能把一个概念用到地老天荒,就像是一本万利的连锁餐厅:菜单不变,只是每次换个国家的酱料。
这无疑是令玩家深感遗憾且失望的,《影》原本拥有刷新系列作品上限的潜力:基础系统扎实,美术演出出色,角色塑造有深度,主线剧情虽然在发售之初引发过争议,但切身体验之后发现它并非短板,甚至称得上颇有深度。但在展开世界探索之后,玩家很快就会撞上一堵熟悉的墙:模板化的支线任务结构。你不是在体验一段段独立的故事,而是在被迫重复一个数据表格中复制粘贴出来的“剧情任务列表”。
这是真正令人惋惜的地方:《影》呈现出的短板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尤其是玩家们早已经吃过了《博德之门3》《天国:拯救2》等“细糠”——哪怕面对庞大的世界和复杂的结构,依然通过手工雕琢的支线,为角色、阵营、世界注入个体命运的重量感。但育碧没有选择“匠心手作”这条路,而是选择像《星空》那样,用“可重复性”来掩盖“不可体验性”的贫乏。

若说育碧用复印机批量生产支线任务,那“双主角系统”就是他们试图靠3D打印制造的“玩法创新”模具——乍一看闪亮登场,其实是新瓶装旧酒。《影》大肆宣传的“弥助+奈绪江”双轨制,早在2015年《刺客信条:枭雄》中就已出现,姐弟搭档、风格互补的设定已有前例。
不过,《影》在叙事自洽性上确实更进一步。按照系列世界观,我们体验到的游戏内容其实是通过Animus或Helix“读取祖先DNA体验记忆”,与《枭雄》章节间自由选择角色的模式冲突。《影》的两位主角任务线各自独立推进,在共享主线任务时,也会在过场动画中明确指出“这是由两人共同执行的任务”。游戏尊重了世界观背景设定,同时也让角色切换在逻辑上具备了合理性。
在操作层面,两款游戏的“双主角差异”也呈现出不同的完成度。《枭雄》虽然试图让伊薇偏潜行、雅各偏战斗,但实战中两人手感区别并不大,只是多了技能升级加点的微调。《影》更用心区分了两位角色的战斗风格:奈绪江动作灵活,主打潜行刺杀;弥助则是力量型战士。但这也造成了明显的游玩体验失衡——在开放世界探索中,奈绪江的游戏体验远优于弥助。当你尝试用弥助跑图、爬鸟瞰点、做探索类支线时,那种生硬迟滞的手感会让你怀疑人生。
一言以蔽之,尽管育碧试图宣称自己的创新性,但玩家只需稍加留意便能意识到:所有“所谓的创新”都曾在系列前作中登场过。育碧只是更加谨慎地进行了优化——仿佛他们害怕再踏错一步,就会把“刺客信条”这个金字招牌彻底砸烂。说到底,《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革新系列传统,它只是小心翼翼地在祖传设计的安全区里“微调升级”,活像一个战战兢兢的继承人,生怕一不留神就毁了祖宗打下的基业。玩家所期待的变革和突破,在育碧看来显然是过于昂贵的冒险,因此我们得到的始终是旧的结构、新的包装,外加一点点无关痛痒的优化调整。
“弥助”之罪:一场本不属于他的文化审判
在《刺客信条:影》正式发售之前,游戏的讨论热度已经被提前点燃——准确地说,是被“点爆”。然而,奇怪的是,这场预售期的舆论战,焦点几乎不在游戏玩法、剧情走向或系统设计上,而是集中于一个角色:弥助。
这并不是育碧第一次因为主角选角而陷入争议,也不是玩家第一次在网络上围绕现今游戏业内的“历史还原”与“政治正确”展开口水战。但在《影》的舆论风暴中,这种情绪达到了一个新高——主角还未走出游戏开场动画,就已经在话语场上“被判无期徒刑”。人们争论弥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配得上“武士”头衔,是否属于“文化挪用”,是否让“刺客信条失去了它的本质”……更有甚者,将这一角色的存在视为对日本历史的“玷污”、对玩家的“挑衅”、对文化归属的“误解”。如果仔细观察即可会发现,许多攻击其实并不集中于游戏内容本身,而归于一个潜台词:“他为什么能是主角?”
这才是整场风暴的核心症结——“弥助”之罪并不在于弥助做错了什么,而是他的位置、他的存在方式、他背后的制作方与文化标签,让他被投射成了一个“越界者”。“他为什么能是主角?”这句话乍看之下像是在讨论剧情安排或游戏架构,实则是一种带着情绪和边界意识的文化本能反应。在围绕弥助的舆论洪流中,这种反应被反复包装为“对历史真实性的维护”,但其实真正被触动的,是对主角资格的潜在共识被挑战。在“弥助”争议的表面之下,埋藏着玩家共同默认的一种情绪:“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必须由时代本身承认的人来完成。”
弥助的问题在于他不是那种“被认同的存在”:他是一个既非白人、亦非东亚的主角,出现在一部描绘日本战国时代的游戏中,还不是作为奇观、工具人或猎奇NPC,而是站在故事正中央的“叙述权拥有者”。这种话语权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看到大量批评将弥助描述为“历史中的异物”:“他只是一个奴隶”“他根本不重要”“除了织田信长没有其他大名认可弥助的武士身份”……
我们能从这种质疑中观察到一种有趣的双标心理:在《战国无双5》《仁王》以及其他日本厂商的文艺作品中,弥助也曾以配角身份短暂出现,却几乎未曾激起任何文化焦虑。但当这个角色成为一部西方厂商作品的核心人物时,舆论却突然破防——这不是角色问题,而是故事由谁讲述、为谁呈现的问题。当一个黑人、一个外来者,站上了一段“我们”的历史舞台,并被赋予了主角的视角,这就触动了某些玩家的文化敏感神经。归根结底,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主角权的民族化焦虑:一部分玩家无法接受“自己的文化”被“他人”讲述,尤其是通过一个“边缘他者”的视角。弥助的争议是一场文化边界感被打破之后情绪反弹的案例,那些说弥助“只是奴隶”“只是杂役”的声音,其实都在无意识地捍卫一个默认规则:主角的位置,应该是由我们想象中的“正统”来占据。即使弥助确有其人,他也应该站在历史边缘。

当我们谈论“弥助”,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
那么,当我们在谈论“弥助”,我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议题的中心从来不是这个具体的个人,也不是这个角色的设计优劣,更不是他是否适合游戏剧情。我们真正谈论的是一个更深层的命题:“谁可以成为叙述者?”
弥助的存在打破了文化默认的权力结构——叙述主角只能来自“内部”,即文化自我书写的逻辑。而《影》让一个异乡人站在历史舞台中央,用他的眼睛讲述这段本应“属于我们”的历史。于是,“弥助”不再只是一个角色,他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主角”不仅仅是故事推进者,更是一种象征性权力的归属标志。谁是主角,往往就意味着谁被赋予了定义故事价值、解释历史意义、拥有行动正当性的权限。
这正是他者最容易遭遇抵抗的时刻,“弥助”被批评、被抵触,恰恰是因为他的设定挑战了许多玩家默认的文化分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日本厂商的游戏、漫画、电影中的出场出现并未激起如此反应——因为他还只是“他者中的异物”,不是“叙述的核心”。一旦他拥有了定义自己故事的权力,玩家的文化安全感开始松动——不是因为他“不合适”,而是因为他“不合格”地站上了“主角的位置”。
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愿意承认,那些原本被放置在“他者”位置上的人物,也拥有成为“我”的权力?以及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本应启发同理心的角色,却成为了争议集中爆发的导火索?为什么我们可以接受“白人勇闯神秘东方”的叙事,但对“黑人在日本成为主角”如此敏感,甚至视之为挑衅?
这就必须谈到另一个更隐蔽但更广泛的文化结构——后殖民身份焦虑与内部等级秩序的共谋。在全球媒体叙事中,“黑暗之心”范式早已成为隐形主线:一个白人进入非西方世界,在异文化中遭遇挑战、自我更新、完成灵魂救赎。这样的故事从《金刚》到《阿凡达》,从《最后的武士》到《仁王》,已经成为全球消费市场最熟悉的剧本。而令人不适的是——东亚文化产业并没有抵抗这种叙事逻辑,反而主动迎合。《仁王》选择白人主角,部分原因就是在海外市场更具“国际化”符号。我们似乎已经默认:如果要让“西方”听我们的故事,就需要一个西方人来讲述。
在这种背景下,弥助的出现分外“不合时宜”。他不是白人,不拥有默认的“文化传播中介权”;他也不是日本人,不符合“本地讲述自己故事”的民族自我书写逻辑。他是夹在主流文化序列之外的“他者中的他者”,在文化等级系统中被编码为最低的那类存在。这个位置使得他的主角身份被视为一种越界,一种对默认“文化等级”的冲撞。
某种程度上,弥助所引发的激烈情绪也是因为我们——尤其是深陷殖民逻辑未解的东亚文化社群——早已无意识地接受了一套危险的三段论:白人居上,东亚居中,黑人居下。于是,当一个“黑人主角”置于“东亚文化”的游戏中,我们面对的不是历史违和而是等级失序,是一个不曾觉察却极其真实的文化代偿结构在被触动。东亚文化圈长期以来习惯于作为“文化被误解者”的身份出现在全球叙事里,但很少反思自身内部的种族结构。在面对《影》讲述的非白人、非本地的“另类主角”时,我们的反应并不是批判性思考,而是集体性的情绪防御。

“弥助”这个角色在《战国无双5》中就曾作为可操控角色出场。
不是所有批评都出于历史忠诚,有些只是源于不想看到自己的文化舞台上站着一个不属于“我们”的人。东亚社群对黑人主角的强烈反弹,很可能源自一种更隐秘的代偿性认同逻辑:在长期被欧美主流叙事边缘化之后,我们亟需一个“文化下位者”来证明我们的相对优势。而当那个下位者被赋予主角光环时,我们的身份坐标就开始摇晃——不是因为那不合理,而是因为我们无法接受自己已不再在食物链上游。东亚社会的种族歧视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模仿未遂。我们未必真正继承了西方在殖民历史中塑造的那种“冷酷的文化优越感”,但我们却学会了那套等级分层的思维逻辑。于是我们用自己曾被压迫过的方式,去看待新的他者——黑人成了这场认同代谢的牺牲品。
余论:谁杀死了刺客?
笔者并不试图为育碧辩护,也并不着力于证明“弥助是一个好角色”,而是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他被如此强烈地否定?我们可以不喜欢一个主角,可以质疑他是否适合这个故事,也可以批评制作方是否真正理解了他背后的历史语境。但在我们动手用键盘打下“我不能接受弥助做战国题材游戏主角”的那一刻,也许值得先问一问自己:我们究竟在捍卫什么?是对历史还原度的高标准要求、对东亚文化主体的尊重,还是某种从未被命名、却已深深内化的等级秩序?
这场争议也像是给《刺客信条》这部作品的当代命运留下了一个无意间的注脚。曾几何时,它是那个站在山巅的游戏,告诉玩家什么叫“自由意志”、什么叫“历史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它开启了整个游戏行业对“历史叙事”的重新想象。如今,它却在被无数作品“致敬”与“重构”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感。它不是失去了独特性,而是那种独特性已经成为了行业标准——而当你成为标准,你就变得普通。
《刺客信条》不是被打败的,它是被模仿致死的。育碧曾经引领过时代,但它没能成为有机的导师,反而僵死成固化的教科书,而教科书是不会被期待创新的。《刺客信条》这个系列曾经是一声惊雷,现在却更像一段回声。《影》更像是一位迟暮的讲述者,终于鼓起勇气换了个开场,却依然要面对被观众打断的宿命。